具体来说,如果仅是以现金财产设立信托,其财产交付和转移都非常容易,设立过程也相应简单。其核心仅在于两个文件的拟定:一是信托设立的信托合同文件;二是信托资金存管的资金监管文件。
但要设立以现金为信托资产的家族信托,信托合同文件如何拟定便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其核心问题包括:信托财产的投资管理;信托受托人的不当管理的监督与法律救济;信托受益人的设定及其变更;信托保护人的法律设定;信托利益在特定条件下的分配等。
对于财产结构以不动产和现金为主的家庭来说,通过遗嘱、信托和遗嘱信托来安排家庭财富的管理与传承问题,目前已经完全可以实现。而对以现金为信托财产的家族信托来说,现金资产信托规避了目前国内信托的登记争议和税收争议问题,可以顺利实现破产风险隔离和财富的转移分配与代际传承,有效保护家庭成员的常规生活和子女的成长利益。
国内目前在这类家庭信托产品方面,已有大量的实践,包括以子女教育和就业保障为目的的现金信托计划,以及和保险产品相结合的保险金信托等。
(二)财产权信托
能不能有效设立财产权信托?由于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的缺失,目前尚存在一些争议。有些权威机构的公开报告认为,在中国“一物一权”的物权法体系下,不能有效设立财产权信托,对此笔者并不认同。
按照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在家庭财富管理过程中可以有效设立财产权信托。原因在于,财产权信托有效设立的关键条件,是财产权的让渡与转移,即委托人将设立信托的财产交付给受托人并发生可以依法确认的财产权转移。
虽然《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应当独立于受托人财产,但由于缺失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目前尚做不到这一点。但根据《信托法》第11条和第16条之规定,并不能借此否定信托的效力。
《信托法》第1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无效:(一)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二)信托财产不能确定;(三)委托人以非法财产或者本法规定不得设立信托的财产设立信托;(四)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五)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信托法》第16条规定:“信托财产与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产相区别,不得归入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受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而终止,信托财产不属于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
以公司股权而论,通过设立财产权信托进行企业传承与治理的安排,实际具有极大的待开发空间。但在此类财产权信托中,如何才能有效防范受托人的道德风险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目前,国内个别信托公司已经设立了以公司股权为信托资产的信托计划,尽管在信托财产的区别登记方面因配套政策的缺失而存在瑕疵,但仍不影响这类信托计划的设立和存续;在家事法律服务方面,通过设立信托来解决婚前财产保护、离婚后子女权益保障和拆迁安置房继受等方面已经有所尝试。
04
发展家族信托面临的法律问题设立家族信托,目前还存在一些制度盲区,需要中国的金融立法和司法部门逐渐填补。如目前中国仅有信托公司能够选择性地开拓民事信托业务等。概括而言,这与当前制度环境下,信托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属性及其信用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信托公司属于须经批准才能领取执照的营业信托机构,受到中国银监会的严格监管。但严格来讲,中国银监会的规定仅能约束营业信托公司。
对民事信托、公益信托而言,按照《信托法》第24条的规定:“受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法律、行政法规对受托人的条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而,在缺失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的情况下,没有“信托业法”或“受托人法”的出台,受托人的道德风险将难以有效防范。
(一)委托人的法律地位问题
如何理解委托人在信托设立、存续及终止过程中的法律地位,是个重要的问题。国外,有些国家和地区设有信托保护人制度,在中国对信托立法的过程中,对此问题应有一定考量,如在公益信托中设有信托监察人制度。
但为何在《信托法》中没有相应设计对信托保护人的规定?按照目前《信托法》的规定,委托人在信托有效设立前后的法律地位是发生变化的。在信托有效设立后,委托人即不再对信托财产享有所有权,在信托存续期间,委托人应被视为信托财产的法定保护人,并根据信托法的规定保护信托财产、确保信托目的的实现;信托终止后,委托人也会在特定条件下成为法定受益人(归复受益人)。
按此理解,则《信托法》的框架非常清晰。按照这样的理解,再根据信托合同文件的约定,合理设定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权利和义务,家族信托设立的目的才会容易实现。
契约自由已经成为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虽然可能也会面临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但只要充分利用法律基本原则和基本法律,完全可以通过合同约定和业务实践来推动信托业的发展。
(二)信托业法的缺失和谨慎义务规则
无论是营业信托还是民事信托,必然都会涉及目前中国“信托业法”尚属空白的法律问题。正是由于信托业法的缺失,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受托人的谨慎义务规则主要依赖于学理解释,包括商业准则下的评判和法律准则下的评判。“信托业法”需要和“信托税法”“信托财产登记法”结合,统筹考虑。在国家治理层面如果已经确立建设强大的财富管理行业的目标和方向,信托业法、信托税法和信托登记法的空白应该尽快得到填补。(三)税收问题撇开信托税法的空白问题,就家族信托和节税、避税的关系而言,税收问题本身也是一个微妙而敏感的问题。一方面,中国贫富悬殊问题仍非常严重,社会普遍存在“仇富”心理,对民营企业是否负有创业原罪的话题一直存有争议;另一方面,特权阶层和贪污问题不断扩大,民众获得财富的机会十分不均等,加重了对待财富拥有者的理性缺失。再者,我国的私权保护状况并不理想,受国家意识形态和司法现状的影响,如避税不当,还有可能引起涉及刑事责任的争议。因而,对于以服务中产以上阶层的家族信托而言,如何才能有效、合法地处理信托与税收的关系,是需要慎重对待的重大问题之一。


 40512/31
4051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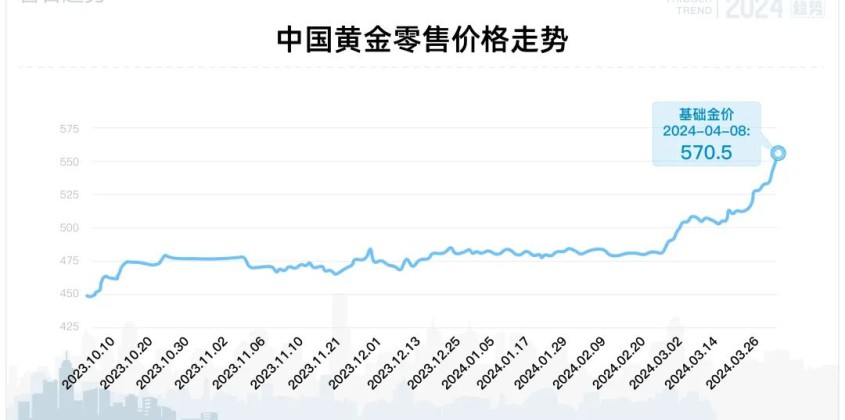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